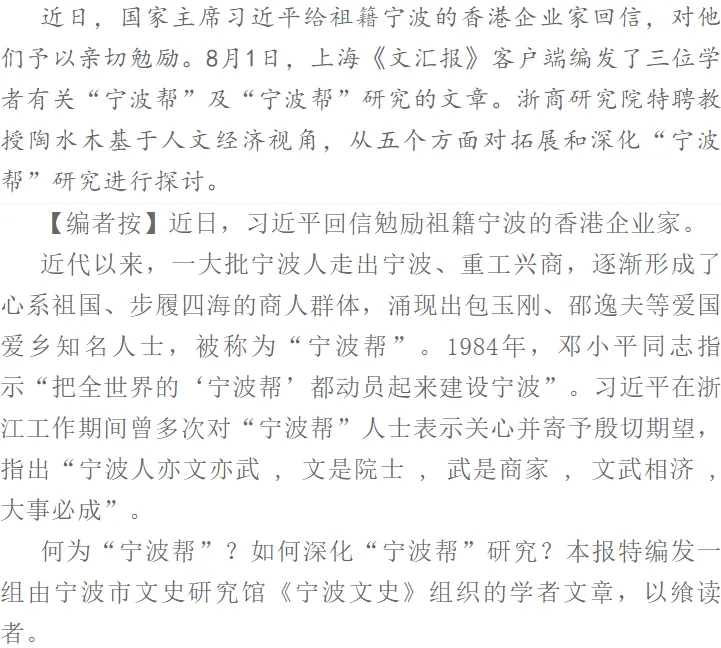

宁波帮博物馆
笔者以为,从人文经济视角,至少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拓展和深化“宁波帮”研究。
一是拓展和深化“宁波帮”经济思想研究。思想是行为的先导和指针,也是行为经验的结晶。作为近现代最具实力和影响力的地域商帮,“宁波帮”商人留下了大量的著述、呈文、报告、函电、讲话、日记等,仅仅将“宁波帮”著名商人虞洽卿、刘鸿生、秦润卿、方椒伯、宋汉章、张静庐、邵洵美、张石川、周信芳、袁牧之等以“作者”在《晚清民国报刊库》检索,就可以发现他们都曾在近代报刊上发表不少著述,相信用其他方法再检索, 肯定会更多, 而且相信更多的呈文、报告、函电、讲话会在相关档案中。所有这些,包含了“宁波帮”极其丰富的经济思想(包括有关文化产业发展的影视、演艺、编导理论),这是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不无遗憾的是,专门研究成果基本上仍是空白。这是遗憾,也是未来“宁波帮”研究的广阔空间。
二是拓展和深化“宁波帮”文化产业研究。文化产业是指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活动,其内涵随着经济社会,特别是科技的发展而发展。近代文化产业主要包括:生产与销售以相对独立的物态形式呈现的文化产品的行业,如生产与销售图书、报刊、影视、音像制品等行业;以劳务形式出现的文化服务行业,如戏剧舞蹈、体育、娱乐、策划、广告、经纪业等;为其他商品和行业提供文化附加值的行业,如装潢、装饰、形象设计、文化旅游等。“宁波帮”是近代出版、影视、游艺娱乐、乐器制造与销售等行业的主要开创者,而且长期居于重要地位,在报刊、音像制品、戏剧演艺、广告策划、装潢装饰等行业也具有重要影响。“宁波帮”文化产业对相关行业, 特别是其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对于近代中国民众生活、社会文化的影响,仍需深入研究。
三是拓展和深化“宁波帮”非文化产业的文化意义研究。建筑、造纸、医药、钟表眼镜、银楼首饰、服装服饰、笔墨文具制造等行业虽非狭义的文化产业,但对文化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宁波帮”在这些行业都具有重要地位,但缺乏对“宁波帮”经营这些行业的文化意义研究。比如建筑业,宁波帮是近代建筑业尤其是上海建筑业一支极其重要的力量。尽管有对“宁波帮”营造厂和其重要建筑的一般性介绍, 缺乏对设计理念、建筑思想、施工技艺、装饰艺术、建筑风格及建筑物对城市空间、业态分布、城市风貌、民众生活等影响的深入研究。比如“宁波帮”笔墨文具制造业中的华孚金笔厂、民生墨水厂(现均属上海英雄集团有限公司)和金星金笔厂都是具有近百年历史的著名企业, 这些企业生产的华孚牌、英雄牌、金星牌、燕牌各类自来水笔、铅笔、绘图笔等及民生墨水,伴随几代人的成长成才成业,见证党和国家许多重大历史时刻,对中国文化影响甚大,也需要深化研究这些企业的文化意义。
四是拓展和深化“宁波帮”文化事业研究。“宁波帮”具有文化情怀,他们在从事产业经营的同时积极投身文化教育事业,如捐资兴学助教,收藏古籍字画,编印出版文化典籍和乡帮文献,热心赞助公共体育、卫生和文博事业。目前缺乏对“宁波帮”教育思想研究,也缺乏“宁波帮”教育、藏书、乡邦文献编印对文化传承、发展影响的深入思考。其实“宁波帮”在上述其他领域都具有影响,例如体育事业,“宁波帮”商人曾发起成立一些体育会、体操会,建设体育场馆设施,赞助各种体育赛事,这些都应从人文经济视角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研究。文化产业经营者如张静庐、张石川、周信芳、袁牧之、邵洵美、应云卫等在从事出版、影视制作、演艺、编导等的同时,也发表了不少关于出版、影视、编导方面的理论文章,更发表有大量剧本、小说、诗词、散文随笔等。对于这些,也需要从人文经济视角再拓展和深化研究。
五是拓展和深化“宁波帮”物质文化遗存与当今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研究。迄今“宁波帮”仍存有大量物质文化遗存,包括“宁波帮”营建的著名建筑,“宁波帮”各类工商企业遗存,“宁波帮”的各类慈善公益遗存,如“宁波帮”捐资的各级各类学校、善堂善会、慈善医院、场馆会所、桥梁及水利遗存, 以及“宁波帮”工商业者的故居旧居、祠堂、墓葬, 等等。这些物质文化遗存记录着“宁波帮”活动的历程和文化积淀,研究“宁波帮”物质文化遗存是“宁波帮”研究的自然延伸,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要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进一步加强对“宁波帮”物质文化遗存的调查,建立文物档案, 加强各类不同文化遗存的保护、开发、利用。要加强“宁波帮”文化遗存的活化利用,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利用“宁波帮”文化遗存建设相关博物馆、文化馆、纪念馆、陈列馆、文化创意馆;要根据不同的文化遗存开发各种文创产品,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文旅结合,发展文化旅游,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
(作者为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院特聘教授陶水木)
素材来源:上海《文汇报》客户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