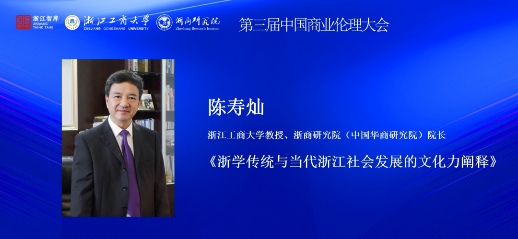当代浙江在各个领域取得的成就为世界瞩目,毋庸讳言,这种成就既得益于中华优秀的伦理型文化,也得益于之江山水所培育的浙学传统。浙学传统是涵养浙江精神的源头活水,也是促进浙江当地社会文化与经济发展的文化力动因。
在这里,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浙学与中国传统的独特关系,特别是宋室南迁之后的浙学发展中所表征的中国文化发展的浙学转向问题。南宋中后期的浙学与朱学、陆学鼎足为三,是为南宋中后期三个主要学派,这是周程理学文脉在南方中国的延续与发展。此后,明代阳明学与清代浙东学则成其为当时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后的原创性高峰以及近代以来启蒙的先声。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我们都无法否认,浙学书写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个特定时期的最为浓墨重彩的华章。正是这个意义上,我认同有些学者所提出的中国传统文化在特定时期的浙学转向。这种转向在《宋元学案》与《明儒学案》中有着极为清晰的脉络:当我们读《宋元学案》时,我们会发现传统文化发展中的明确的浙学话语强势;当我们进而再读到《明儒学案》时,我们就会发现,在当时的中国思想界,以浙江为中心,浙学话语特色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特点。
浙学发展的过程,也是创新进取、兼容并包的浙江精神的文化基因得以孕育的过程。以宋代的浙学发展为例,我们可以清晰地体会到浙学发展与浙江精神文化基因的孕育。北宋初期,两浙路尚未有在思想史上有影响的大儒。即便如此,北宋初期的两浙路学者之于浙学兴起奠基意义不容忽视。
当时,成为后来浙学兴起的奠基人主要有:
(1) 胡瑗的门人或受胡瑗“苏、湖教法”影响的人。胡瑗在宋明宗明道、宝元年间受范仲淹之邀,于浙西平江府(今苏州)讲学。胡瑗对浙学的兴起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他所开创的“苏、湖教法”促进了当时地方政府的办学积极性,两浙各地兴办不少学校,从而培养了-批有志于儒学的学者,如滕元发、顾临、徐中行等。浙学贤达中受其影响的还包括了永嘉王开祖,继之有丁昌期;杭州有吴师仁;浙东则有“庆历五先生”——杨适、 杜醇、王致、楼郁、王说。北宋时期,这批浙学的早期贤达大多隐居乡野,讲学授徒;他们学问深醇、志行高洁而不求闻达,但却培养了更多的浙学后学,成为浙学最早的奠基人。 (2) “北宋五子”的门人。这些人大多传道于乡野,虽然在思想史上影响有限,但他们却在浙学渊源处确立了浙学兴起的始基。北宋末期,“元丰太学九先生”在承继关学、洛学的同时,开创了浙学的事功学术,这种学术创新与张九成的儒道融合以及后来婺学向历史哲学的转向都充分体现了浙学在学术上的创新进取精神。
朱学与象山心学的后期发展主要是由两浙学者承继并加以宏扬的:
朱学在朱熹的主导下鼎盛一时,但朱子之后的朱学发展主线却在两浙路而非福建路。朱门弟子中,出身两浙路者甚众,影响者较大甚众。朱熹之后,承朱学衣钵者是黄幹;黄斡之后,福建路基本没再出朱学大儒,而两浙路则成为朱学发展的最主要区域。南宋朱学在两浙路的发展分为两支:一支是被称为嫡传正宗的“金华学派”,其代表人物是黄翰弟子与再传弟子中人称“北山四先生”的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他们创立的“金华学派”被学读为“金朱学”。另一支是“四明朱学”。代表人物是王应麟、黄震、史蒙卿等。 象山心学的传承与发展在两浙路的成就也远甚江南西路。陆渊原本是江南西路出身,其门人中也以江南西路者较众。但两浙路出身的象山门人亦众;象山之后,陆学弟子中的学术功绩与地位最卓者乃浙东出身的人称“甬上四先生”的杨简、袁燮、舒瑞与沈焕。陆学本籍的江西门人的影响远不及“甬上四先生”,据《宋元学案》记载,“甬上四先生”成为陆学传承的最主要力量。这支心学力量也成为明代阳明心学的学术渊源,阳明原本四明人氏,他学术思想自是必定受了这一支心学学派的影响。
从朱学及象山心学在两浙路的传承与发展看,南宋两派影响最著名的学派思想都是得以依靠浙东学术力量才得以光大,而两浙路的学者们继承与光大朱学及象山心学的同时,也开创了自身的浙学传统,这其中所体现的不仅是创新进取精神,更是体现了兼容并包的学术精神。
浙学的发展所揭示的重要文化命题在于:浙学自宋代以来的发展与宋室南迁有着密切的关系,宋室南迁成就了包括浙江在内的江南区域的经济与政治中心地位;而这-经济与政治中心地位又势必成就某种独特的文化地位,也就是说,当一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逐渐成为区域龙头之后,该地区的文化发展也必将引领那个时代的文化发展。以这一路来审视当代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我们或许可以说,当代的浙江经济、社会的发展必将伴随某种文化的繁荣与强盛。浙江一直行进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潮头阵地,温州模式、浙江奇迹等彰显了当代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20世纪90年代以来,浙商更是创造了浙江发展的新景观:作为浙江省会的杭州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电子商务中心、全球移动支付大本营、世界一带一路总部所在地,等等。但如果深入反观、思考的话,我们总会感觉到当代浙江发展与传统浙学之间的某种疏离:当代浙江发展所代表的文化及其内在的精神到底是什么?这种文化与内在精神是如何在传统中创新而来,又将在何种方向得以光大宏扬?
说到文化力命题,马克斯.韦伯曾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关于经济、社会发展与文化力关系的一般性命题:任何形态的经济、社会发展必定内蕴了某种文化力的支撑。没有这种文化力的支撑,任何形态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既无法解释,也不可能。在这个意义,我们回过头来看当代浙江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我想人们不会怀疑其所取得的重大成就。然而,在韦伯的文化力进路上来审视当代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我们就需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那种使得当代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的文化力支撑因素到底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既关乎对浙学文化传统及其现代转型,又关乎当代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文化解读、解释,以及对其面临文化问题的解决、未来发展的文化策略,等等,不可谓不重。吾辈当深思之,慎虑之!